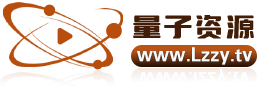于尘埃中仰望忠魂,宋禹演绎小人物的人性史诗 -
如今不少影视作品热衷于塑造天赋异禀、使命加身,站在道德与能力的巅峰,以“开挂式”成长横扫一切困境的完美英雄,尤其是在如今的短剧赛道尤为明显,皆因这样的角色带来的爽感,确实迎合了许多观众释放情绪的观剧需求。但这类题材虽然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情绪价值,但却往往难以触及观众内心最深处的共鸣,因为真实的人性,从不在云端。
就当“短国”里霸总、王爷漫天飞之时,短剧《白发老卒》却作为一个反套路式存在出现在观众面前——它将视角对准了历史中的小人物,一支由老兵、舞女、学徒等组成的前往孤城龟兹传达敕谕的小队,他们在安西古道的风沙中踉跄前行,用卑微的生存本能对抗着时代的洪流。而宋禹饰演的“逃兵”曹阿奎,便是这群小人物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

这个一出场就是与酒壶为伴,浑噩度日的混不吝,却也有着辉煌荣耀的过往,作为安西唐军的一员守护边疆。只因军队出现叛徒导致城防图被盗,所有出生入死的战友都战死,唯有他一人背负着替生死弟兄们送家书的承诺苟活于世。从此,这世上多了一个被酒精麻痹的破碎灵魂,少了一个雄视黄沙的战士。在剧集的前半段,宋禹用微驼的脊背、涣散的眼神和颤抖的双手这个肢体语言,让观众瞬间代入角色的颓废底色;但当得知三爷也是唐军老兵,要向龟兹传达敕谕时,他原本涣散的目光顿时变得如火如炬,迸发出锐利和坚定,流露出封存已久的军魂。这种“形”与“神”的精准把控,让曹阿奎的转变具有可信的说服力。
与那些被光环环绕的大英雄不同,曹阿奎这个角色的身上充满了人性的弱点与挣扎。他自然不是一个天生的勇士,而是一个被命运与背叛击垮的普通人。他身上没有苟且偷生的幸运,身上背负着的是幸存者的沉重负罪感,是“战友皆死我独活”的内疚,是“欲死恐负同袍托”的惶恐,也正是这种纠结与矛盾,使得他的自我救赎之路更加动人心魄。
有人说,死是最容易的事,活下去反倒是需要勇气,尤其是像曹阿奎。替战友送家书的承诺,是支撑他宁愿背负逃兵骂名也要活下去的理由,而这也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梦魇。宋禹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这种负罪感转化为一种可见可感的情感。在他涣散的眼神深处,隐藏着无法言说的痛苦,仿佛对世界毫无眷恋,在他颓废的外表下,深藏着是对过去无法释怀的执念。
就是这样一个逃兵,在新的羁绊中找到支点,敕谕小队的出现,成为了他重新连接世界的纽带。宋禹并没有简单将角色的转变一笔带过,而是细致地刻画了曹阿奎与敕谕小队其他成员从疏离到信任的互动过程。起初,他对这个群体充满戒备,仿佛一只受伤的野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伤口。而随着剧情发展,他内心深处被封存的忠诚与守护本能被一点点唤醒。这些新的羁绊,成为他灵魂重建的支点。
曹阿奎最终的断后之举,不是被迫的牺牲,而是清醒的、主动选择的归宿。这是他对于叛徒的复仇,是对新同伴的守护,更是对安西军精神的最终证明。他以一己之躯完成了对“忠魂”的终极诠释。他的死亡不是英雄主义的悲壮谢幕,而是一个凡人用血肉之躯叩问生命意义的悲怆仪式。宋禹用自己精湛的演绎,完成了一个灵魂从破碎到重建,宋禹让“忠魂”在小人物的身躯中发出最灼热的光。
可以说,《白发老卒》与宋禹的相遇,是一场演员与角色的双向奔赴。对于演员而言,曹阿奎这个复杂、立体、充满悲剧色彩的角色,为宋禹提供了突破“类型化”桎梏的契机;对于角色而言,宋禹的演绎赋予了其超越文本的厚度。当观众为曹阿奎的死亡潸然泪下时,他们感动的不仅是剧情,更是基于相信的力量。
正如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所言:“真正的崇高,在于承认人类的渺小。”《白发老卒》与宋禹的表演共同证明:动人的艺术从不需要炫技式的呐喊,它只需要一颗敢于直面人性深渊的赤子之心。在这个AI生成内容泛滥的时代,这份对表演的敬畏,或许才是最珍贵的“忠魂”。

在裂缝中雕刻人性,于无声处听惊雷,正是演员宋禹的表演哲学,在过往的作品中,他向来擅长通过平静中蕴含震撼,克制中饱含深情的表情与动作刻画,来塑造多元角色的内在情绪张力。

在电影《浴血誓言》中,他是红军营长牛大勇,刚硬铁血又充满柔情;

在《冰雨火》中,他将境外头目二两的狠辣与脆弱糅合成极具压迫感的反派形象,

从重大革命历史剧《中流击水》中复杂多面的蒋介石,

到历史题材大剧《大道薪火》中有银行家的缜密,又有革命者的赤诚的毛泽民,

始终致力于挑战不同类型角色的宋禹,在今年迎来了又一次大爆发:仅仅是这个月内,就有一部电影和两部短剧上映播出。其出演的《大秦文公》,日前更是进入2025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多彩中华”民族题材电影展映单元。从安西老兵到西陲霸主,他不断拓宽表演的边界,却始终保持着对角色灵魂的虔诚叩问。